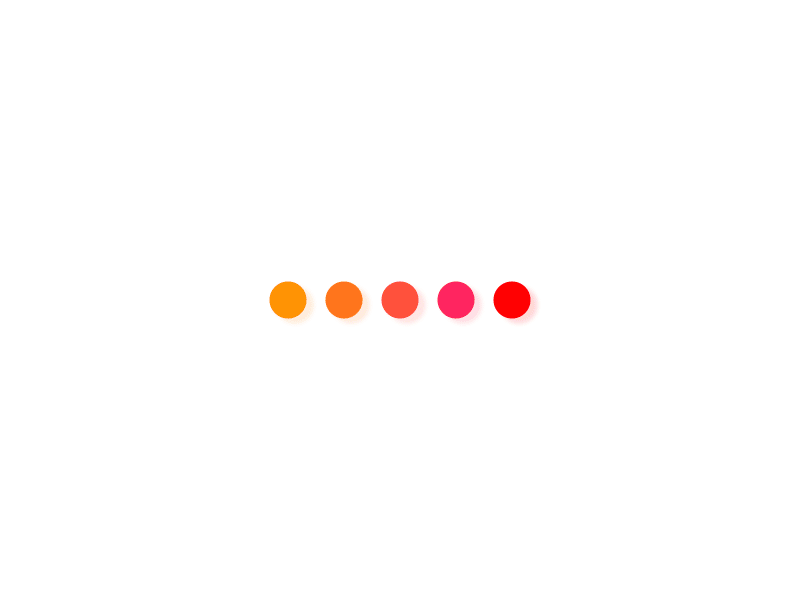据说,以“移步换景”来形容那园子都嫌太粗疏了。在那里,你只要身子稍稍俯仰,目光微微流转——甚至一阵风过,眼前风景都会发生变化。此园号称“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假山亭池暂且不说,房舍营饰亦是独出心裁:窗棂由带花梅枝拼成,楹联则题于竹节蕉叶,为了最佳的采光效果屋檐可视晴雨翻转······四下环顾竟无一寸匠心不到,连房壁都饰以冰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
这座园子建成于340年前。那个夏日的上午,前来祝贺的友人络绎不绝,主人自是感激,跑前跑后热情地招待着。
客人们啧啧称奇着一路走来,好半天才到了客厅。厅壁绘有大幅云烟花树,众人正自欣赏,忽闻头顶鸟鸣,仰观却见枝头羽动叶底翎张,彩墨间竟舞起几只鸟来,不由得人人色变,疑为仙笔。惊魂定后仔细打量,原是于画中松枝间插根铜管拴只鹦鹉,再用拳曲松枝编个笼子囚对画眉,真鸟假树,云遮雾罩浑然一体。回过神来,大家不觉齐齐拍案叫绝。
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赞叹声中,这座占地不过三亩的玲珑园子得了个有趣的名字:“芥子园”——“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
芥子者,极微之物也;佛典有云,一粒小小芥子,也能纳下广大庄严之须弥宝山。
送尽宾客后,疲惫的主人立在门前,久久地凝视着自己手书的对联:“因有卓锥地,遂营兜率天”,眼中似乎有些晶莹。
墙头,几树榴花探了出来,开得正闹,红云一般,为芥子园添了不少喜气。
深冬的一个清晨,我面对着芥子园。
站在浙江兰溪市郊的兰荫山脚,我知道,眼前的园子,其实只是当代的建筑,是兰溪人民为了纪念当年的芥子园主——他们的同乡——而建的一个仿古园林;真正的芥子园应该远在南京。
然而金陵南郊的那粒小小芥子,没抗过三四个世纪的冰霜雨雪,早已被磨成齑粉,随风洒入了浑浊的秦淮河水,再也不存丝毫的痕迹。当年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妙园,如今只能根据园主遗留下来的文字,一笔一划地在泛黄的纸页上描摹勾勒,东鳞西爪地拼凑出一堆潦草而黯淡的零碎影子。
世间已无芥子园。
但莫言此园非彼园。正如先人已然重归尘土,曾经的款款言笑尽皆干涸成神主上的一个名讳那样,天地间终究只剩了这么一方凭吊芥子园主的去处。
能不凭吊吗?无论是戏曲,小说,还是诗文,甚至园林、建筑、出版,谁能装作视而不见,绕开那位明末清初的芥子园主、说不清道不明的文人李渔呢?
裹紧衣领,侧身避过十二月的寒风,我走进了兰溪芥子园。
在园中,我首先寻找一尊雕像。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到,园子里有他自己的一尊小像:手执纶竿,头戴笠帽——李渔自号笠翁,坐于石矶之上垂钓。
我看到的李渔像,手中握着的却是一卷书。
执竿还是握书其实不重要,我真正想看的,只是李渔的手。尽管我清楚,雕塑家宝贵的精力不可能耗费这些细节上,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李渔应该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手。
在我想象里,那双手从背面看去,十指纤长,皮肤洁白细腻,明显属于养尊处优的文人;而翻转过来,却是干枯如树皮,生满了粗糙的老茧。
因为他又是一个渔夫,紧紧握了半辈子钓竿。
他的钓竿,就是一管细细的毛笔。那管笔对李渔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最合适的:“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
这位以笔为竿的渔人钓的是秋风。
打秋风,指的是借助自己的名气游走各地达官富绅之门,以求获得多多少少的资助。李渔是史上最为著名的秋风客之一,自称“终年托钵”,“二十年间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钓钩布满山南海北。
既是垂钓,便需鱼饵。李渔的招牌在当时十分响亮,时人王安节曾言:“(李渔)名满天下,妇人稚子莫不知有李笠翁。”康熙年间刘廷玑《在园杂志》也载:“李笠翁一代词客也。著作甚夥,造意创词皆极尖新。”更妙的是,他的创新不只限于文章,恨不能对世间万物都琢磨改造一番,如光绪《兰溪县志》云:“性极巧,凡窗牖床榻服饰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仅凭这两点,便已有做上等清客的本钱,况且李渔还有压箱底的饵料:他游荡江湖,竟然随身带着一个戏班!
李渔一生涉笔多种体裁,但最出色的还是戏曲与小说。他自兼编剧与导演,自己训练演员——事实上演员便是他的姬妾,如此一手炮制出来的戏班自然非同小可,无疑是当时第一流的档次,大佬高官贺喜过节或是闲极无聊之时,若是眼前忽然出现这么一群妙人,岂不欣喜若狂!
风灯一盏盏高悬,红氍毹一尺尺铺开,鼓点冬冬响起,伴着一声柔肠百转的长叹,曼妙的佳人款款登场······
偷眼瞧见东主伴着节奏摇头晃脑并指轻敲,李渔拈着瓜子,得意地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一竿又将有个不薄的收成。
在园中,我见到一幅标示李渔游踪的地图。交错的红线,织成了一张软软的蛛网,一丝丝曳着袅袅余音,优哉游哉,在轻歌曼舞中拂过了大半个中国。
李渔的朋友,著名文人尤侗对这种华丽的秋风手段曾有描述,笔端不无艳羡:“笠翁薄游吴市,携女乐一部,自度梨园法曲,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
掌声再响,“日食五侯之鲭,夜宴三公之府”的“神仙中人”毕竟只是一个迎合东主的高级文丐,何况率领姬妾组成戏班巡回演出的方式格外刺道学君子的眼,于是不少人提起“李渔”二字,口中不免带些轻视:“人以俳优目之。”
有人干脆破口痛骂:“李渔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亵。常携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也!”
尽管其中很多文辞只是恶意扭曲的污蔑——也许同行真的是冤家,留下这段文字的是同样“喜作词曲小说”的袁于令,但李渔对“善逢迎,游缙绅间”这个断语是绝无反驳之力的。
后人提起李渔明显也有莫大的遗憾,《品花宝鉴》中孙仲雨的话很有代表性:“做《十种曲》的李笠翁,不能做个显宦与国家办些大事,遂把平生之学问,奔走势利之门。”
当时就有很多好心人对李渔的生活态度不以为然,替他感到不值。他们质问:难道你李渔不靠秋风就过不下去了吗?
如他的好友毛稚黄便点明:“卖赋得金者,相如以后如翁者原少。”意思是能把文字卖出好价钱的,千金一赋的司马相如之后,你李渔也算数一数二了。
此言不虚。李渔颇有经济头脑,他卖曲、卖文、编集、印书,文字生意一直红红火火,要说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并不困难。你李渔终年捉襟见肘,其实只因你居家太多耗钱的名堂了!你李渔出名的爱园林、爱美女、爱鲜花、爱锦衣、爱美食,自身却不过一介布衣,俸禄毫无祖产寥寥,“无沟洫之纳,而有江河之泄”,不穷才怪!
“亲戚朋友鄙而笑之者亦复不少,皆怪予不识艰难,肆意挥霍,有昔日之豪举,宜乎有今日之落魄。”(李渔《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
对这种抱怨,李渔除了再叹几声生计艰难,并没有多加解释。
转过身来,他涩涩一笑,活动活动手腕,又轻轻地抓起了那管笔,优雅地伸向了江湖。
初读李渔,于打秋风之外,我对他还有更大的不满。
明清易代,异族入侵,一时间有多少烈士豪杰挺身而出浴血卫国,而你李渔在日后却不止一次提到,躲避战乱隐居兰溪乡间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活:“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
当山河沦陷,清人的刀锋劈向江南时,李渔正是年富力强的三十五岁。
你李渔平昔好以李白后人自居,口口声声“我家太白”、“我家太白”,你难道忘了你家太白一生治国安天下的抱负吗?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胡沙漫天之际,你这“太白后人”居然躲起来享着“列仙之福”——
铁蹄声中轻轻敲起一阵战战兢兢的鼓乐,你竟还纳了个标致的小妾!
再看李渔的作品。
李渔笔下,无论戏曲小说,尽皆在风花雪月中变幻身姿,“十部传奇九相思”,毫无国破家亡的感慨,甚至还曾将北宋徽钦二帝被掳北上做为主人公重获自由的天赐机缘。若与当时同样著名的《清忠谱》、《桃花扇》之类苍凉悲歌相比,简直只是一团团粉红色的靡靡香雾。
李渔降世之初,父祖为其取名“仙侣”,字“谪凡”——
莫非你李渔果真从天而降,绝不关俗世点滴兴亡?
读着李渔的生平,作为乡党,胸中常常憋着口郁气,有时恍惚起来,似乎李渔便在面前,忍不住便要戟指责问。
可就像一拳打在烂泥潭上那样尴尬,李渔只用两句诗就让我指了个空。
康熙九年,李渔游到了福建。八月七日,是李渔六十大寿生日,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收礼机会。于是,他遍邀宾客在寓所大大操办了一番。
寿筵很成功,李家戏班使出了浑身解数,连李渔自己都被起哄上台唱了曲,气氛狂热得几乎掀散了屋瓦。
酒阑客散后,醉眼朦胧的李渔看着筋疲力竭的姬妾哈欠连连地卸着装,仍然意犹未尽。他呻吟着喝了口浓茶,忽然想到了什么,踉跄着走到桌前——桌上还摆着客人写寿联时备下的笔墨,他提起笔,要为自己写首寿诗:
“自知不是济川材,早弃儒冠辟草莱······”
这十四个字,坦率中带几分苦涩,辛酸中有几分狡黠,让我所有的愤慨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一派空荡荡的失落。
你看,他已经老老实实坦白了,知道自己朽木难雕,狗肉上不了席,所以早就识趣地离开了儒家门墙——
你们难道忘了我李渔尽管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也还是彻底放弃了举业吗?
可你们还总指责我“不为经国之大业,而为破道之小言”,硬要把那副血淋淋油腻腻世代传承的重担往我瘦削的肩头上压,岂不是驱羊耕田、一厢情愿?
身子轻轻一扭,李渔便从那座篆满“兼济天下”、“建功立业”等红字的东方须弥山下溜出身来,
站到了一片草莱之中。
那个雨后的清晨,初醒的李渔闻到了一阵清香,起身来看,草莱间开了几朵茉莉花。他很是欣悦,拣好的摘下几朵,顺手往鬓间插去,不料竟插空了。
原来满清的薙发令已经行到李渔的头上。
苦苦一笑,他将花儿揉碎,扔到了路边。
“便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
即使在文字上也没有多少当时文人很普遍的激烈反应,只几声苦笑,便在李渔身上完成了改朝换代,前明生员从此成了大清顺民。
弃在道旁的,除了那几朵残破的茉莉,还有一项沉重的儒冠。
头顶无冠,鬓间无发,倒也一身轻松;但轻松之余,忐忑的李渔也应该感到一阵深深的凉意。
他将为自己戴上个什么帽子呢?
“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笔蕊生心,非托微言以讽世。”
这是李渔自撰《曲部誓词》中的两句话,很清楚了,李渔新的身份是“砚田糊口”的卖文商人。
誓词中接下去的文字更像一个商业声明:“沥血鸣神,剖心告世”,我李渔作文绝无攻击时政讽刺世人之心,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若是“稍有一毫所指”,甘愿三代哑口!就算在阳间侥幸逃脱报应,到了阴司也照样受罚!
我著书绝不为名山事业,更不奢望流传千古,谁都不必徒劳心神地在我笔下找什么微言大义。我知道人们最需要什么,更知道卖什么最安全、最皆大欢喜。
笑声,我知道这个苦难的人世间最缺少的是笑声。随你说我粉饰太平也好、安抚创伤也好,反正我的宗旨是“传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我忧”;人人原本都是悲剧中人,都有那么多摆脱不了的烦心事,来看戏原本就是为了暂时逃避一下,我干吗不托着他们离地三尺,痴痴醉醉欢欢喜喜飘摇三两个时辰呢?
翘起二郎腿仰躺在后台的竹椅上,眯眼低低地按着节拍,听着观众随着剧情的起承转合一阵阵哄堂,李渔红光满面。
“(笠翁《十种曲》)意在通俗,故命意措词力求浅显。流布梨园者在此,贻笑大雅者亦在此。”这样的评价,原本就在李渔预料中,他点点头并不否认,但慢悠悠地吟了一句:
“阳春白雪世所嗔,满场洗耳听巴人。”
对于一个商人,阳春白雪往往意味着生意萧条呀。
作个揖道声失陪,李渔又忙着起草反盗版宣言去了:
“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
李渔的作品之所以畅销,也是因为他的每出戏每篇小说,主人公都能得个圆满的结局。
也许是刻意回避敏感的政治题材,也许是他的偏爱,李渔作品的主角大都是才子;而才子最终都能得享艳福,匹配佳人。
不只喜结良缘,才子常常还能金榜题名,富贵双全——
李渔从来舍不得让任何一位才子在他笔下受委屈。
李渔委实为他的才子们耗尽了心机。都说他的作品构思奇巧,其实奇巧大半都在中间部分,至于两头,不外是才子佳人缘起、缘成;所有人都了然主角必然能梦想成真,但摆在眼前的却常常是山穷水尽的一副死棋,绞尽脑汁也找不出突破口——于是卖点来了:且看你李渔如何解开自己设置的这个连环,怎么将那根红线穿过冰冷的铁板系在等候多时的那只脚上。
一路看来,两三下起落,四五个腾挪,喜庆的鞭炮便炸开了一条铺着红地毯的大道。随着狂欢的唢呐奏起,才发觉早已经拍肿了大腿。
用风筝,用倒影,甚至用当时刚传入中国的望远镜,李渔总是能独辟蹊径,用前所未有的离奇方式完成一个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渔这种呕心沥血的巧思,除了商业因素外,应该还蕴含着他一个简单的标准:既然是才子,便不应该受到亏待,理当享受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何况天下万物的美好之处,也只有真才子才能发现,才能受用。这种心态,在《闲情偶寄》中表露得很多:只要在一些凡人熟视无睹的事物上有了心得发明,或是独具慧眼找到出一种崭新的行乐法子,李渔总忍不住要跳出来拍着胸脯自吹自擂一番,那种可爱的得意几百年后还令人莞尔。
“因有卓锥地,遂营兜率天”,只要入了我笔端那点卓锥之地的才子,我李渔便有责任为他营造一个极乐的兜率天宫。
可才子佳人写得越多,李渔心中就越不平衡。
在纸上,他可以做一名有求必应的仁慈上帝,孜孜不倦地为虚构的才子谋划幸福,但现实中,他自己的上帝又在哪里呢?
创造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才子的人,难道不是更大的才子吗?
有次与朋友通信,李渔满腹牢骚地发泄了一通:
“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踘、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
无论是谁,只要掌握一门手艺,下棋也好,说书也好,唱曲也好,都能免于贫贱,成为王公大臣争相供养的座上宾;我李渔“识字知书”,作品“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使数十年来无一湖上笠翁,不知为世人减几许谈锋,增多少瞌睡?”如此“谈笑功臣”,却常常陷入到“饥不得食,寒无可衣”的窘境,这何其可悲、何其可悯——
你说我饥寒交迫是夸大其词吗?你该明白,才子的衣食原本就不只是为了温饱,我听歌看曲、纳小妾、吃螃蟹,那是涵养才气的必须,更是才子应得的本分!我李渔多才多艺,境界岂是说书唱曲之流所能比拟万一,理当得到更好的供奉。
再说别的开销倒也罢了,要圆满我生平最大的梦想,造一处自己的庄园,光靠笔头那点生息简直是杯水车薪,猴年马月也实现不了。
“予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
这个梦李渔已经做得太久了,以至于将一部小说集命名为《十二楼》,每篇都以楼为名——他这是用笔墨过一把造园的干瘾呢。
《十二楼》的末篇,李渔写了一个绝意进取的隐逸之士得到一帮疏财仗义的官绅阔佬的大力帮助,建了一座称心庄园。谁都看得出来,这是李渔夫子自道,写他自己的一个美梦。
但小说只是小说,梦也到底只是梦,李渔很清楚,要建庄园,坐在家里等上一万年天上也落不下一砖一瓦。
看来,那座配得上笠翁才气的兜率天宫,只能我自己出手营造了。
很自然的,李渔的眼光投射到了烟雨迷濛的江湖。
随着一声叹息,有缕秋风从稿纸上楼阁戏台的草图间生起。
于是,天地间有了那么一座芥子园。
但兰溪芥子园的主要建筑“燕又堂”,其名却得自李渔早年在兰溪乡间牛刀初试所营造的伊山别业,资金来源除了一点可怜的祖产,基本靠举债。
李渔在伊山北面修了个“且停亭”,并手书一联:
“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
在这里,李渔将原名“仙侣”改为“渔”,为此还写了一首小词《忆王孙》:“聊借垂竿学坐功,放鱼松,十钓何妨九钓空”;并有诗云“但作人间识字农”,俨然要在此渔耕度岁了却余生。
三年后,李渔卖掉伊山别业,移家杭州。这便是李渔一辈子念念不忘、反复念叨着享了“仙福”的三年。
燕又堂里陈列着李渔的资料,在显眼处,有阙《多丽·过子陵钓台》的词。
那是李渔六十五岁时所作。
那年夏末,李渔泛舟富春江,亲送两子赴浙应童子试,经过了严子陵钓台。
江水澄澈,青山如画。想起那位坚辞天子挽留的著名高士,再回头看看自己这几十年,站在船头的李渔不由得感慨无限。
他一定忘不了两年前游走京师的那些难堪经历。达官贵人们或是揶揄讥讽或是冷若冰霜,敷衍几句再端茶送客还算是留点面子的,不客气的干脆给你个闭门羹;连连碰壁,他脾气再好也有些懊恼,便在寓居的客房门口挂了块“贱者居”的匾;可次日却发现对房也挂出了块匾,上面赫然是“良者居”三个大字,虚掩的门后,时不时传来一阵骄横、不屑,或是猥亵的笑骂······
那回京城行还有件事深深触动了他。有次当他拜访一位朋友时,在书桌上发现了一张当票,票面十二两,抵押物是主人珍爱的古董——而就在前几天,他得到这位朋友的一笔赠金,正好是纹银十二两。
李渔不禁面皮发热,慢慢低下头去。轻溅的浪花,将他扭曲的倒影一次次地拍成浮沫,看了一会,他的额头渗出汗来。
好在竹篙几下疾点,轻舟便飞速地驶向了下游;转了几个弯,终于远远逃离了钓台。李渔这才悄悄舒了口气,沉吟了许久,回舱取过笔墨,填了一首词。
“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
同为钓客,在您面前,高卑何止千倍,我李渔无地自容啊!
“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 低声喃诵着最后一句,李渔扭头凝视着身边的一双未脱稚气的孩子,目光中充满了希冀。
“前面就是桐庐县了!”这时耳边传来艄公的提醒,李渔精神顿时一振。他下意识地整整衣衫,站起身来。
他知道,桐庐县令已经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正焦急地等着他。
当然,少不了还有一份馈赠。
临到老年,俯视流水,李渔看到他自己的形象是“面目堪憎”;那么我看李渔,又是一张什么脸孔?
在芥子园里,我竟然有些惶恐起来。
我已经发觉,离李渔越近,他的身影便越是模糊。
读到弃儒冠的诗句时,我原以为搭住了李渔的脉搏,但不久我的信心就开始了动摇,反复问自己:简简单单一句“自知不是济川材”真能解释李渔的一生吗?
我似乎有些懂了当年李渔的朋友许茗车说那番话时的无奈:“今天下谁不知笠翁?然有未尽知者。笠翁岂易知哉!——止以词曲知笠翁,即不知笠翁者也!”
也许,是几千年的辉煌与苦难使我们习惯了仰视,习惯了欣赏海水天风重峦叠嶂,习惯了崇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习惯了敬仰须眉倒立昂首挺胸——
所以,当视线中突然出现一粒芥子、一片草莱时,可能就使我们不知所措了。
尤其是那支给我们留下太多“摇撼五岳、惊泣鬼神”雄伟印象的文人之笔,居然掉转方向俯身化作了一支钓竿,我们一时间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从前李白渴望做一只搏击九天的大鹏,渴望着有朝一日“仰天大笑出门去”大济苍生,而以“太白后人”自豪的李渔,却日夜谋划着躲入那粒小小的芥子。
但李渔果真能如他自己所说“我能用天,而天不能窘我”,用一粒芥子造出一个称心如意的笠翁世界吗?
燕又堂前,有个不大的池子,隆冬季节荷枯鱼懒,水平如镜。我忽然很想知道,李渔在严陵江水中,有没有看到一座影影绰绰的须弥山。
李渔在池边握书置膝,架足悠闲而坐;微微扭头,目光既不在燕又堂上,也没对着那座临池的精致戏台,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着不远的前方。
李渔认为,万人万物都是欣赏的对象,正如他设计窗户必使两面俱是好图:以内视外,固是花鸟山水;以外视内,亦为扇头小品——
我视笠翁浮光掠影如雾里看花,而他视我等世人,又是一副何样风景?
会不会在他眼中,严陵江水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漩涡,而真正的须弥山,却重重地压在世间每个自以为是的人的头顶呢?
是的,这座大山不知压住了多少豪杰,更不知有多少英雄大吼一声弯腰下去,试图扛起它——甚至可以说,一部二十五史,便是人们在山下的挣扎史、奋斗史。
然而,面对这座山,就只该有硬顶这一种生存方式吗?
李渔神情放松而坦然,唇角隐隐有丝笑意。
与李渔像对视多时,我终于落荒而逃。
临出门前,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但园中的景致已经全部隐藏在那面照壁背后,壁上是四个楷字:
“才名震世”。
2009.1.17